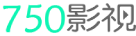甲骨文中的“每”字,在为数不少的甲骨上可见。其上部,不是“艹”,应该也不是“屮(chè)”,而是“加笄于发之形”;下面是“母”或“女”。甲骨文中的“每”,是同源分化字,不是后来所说的会意或指事字;甲骨文中的“每”仍带有“母体字”的含义,但有了更多新意。
一,在甲骨文中,“每”字下面为“女”的更多,仅在“三期甲一九0八”等少数甲骨上为“母”。徐中舒先生说:“从女从母无别,其上像加笄于发之形”。这大约是因为“母”字是从“女”字分化而来——许慎说,母字像两手抱着孩子,或者像人乳。 二,于省吾先生认为,“母”和“女”是同源分化字;“每”和“母”也是同源分化字。他说:“每字的造字本义,系于母字的上部附加一个✔️画,作为指事字的标志,而仍因母字以为声。”

三,王蕴智等中青年学者,同意于省吾先生“女”、“母”、“每”等字是同源分化的观点,但不赞成将“母”、“每”划入指事字范围。他们举出了自己的理由,这里不详赘述。他们认为,这一类字是甲骨文造字过程中特有的现象,称之为“借形变体字”或“变体分化字”更为妥当。这个说法有道理。 四,“借形变体字”或“变体分化字”是怎么回事儿呢?在商代,文字的一字多义即一个字承担记载多词的现象大量存在。当时的人们,为了控制这种“兼职”,在造字的基本部件不足尚且不规范的情况下,于是采取了在某一“母体字”基础上,或通过加上点、横、八、叉、口、0等简单笔画造出新字以示与原母字的区别;或者改变“母体字”的局部结构派生新字。如老和考、月和夕、女和母、母和每、斗和升、大和夫、口和曰、北和非、又和尤、人和千、白和百、子和巳等等。 五,这些新字已经不再是单纯利用表意性符号来作图示,而是使新字进一步符号化和抽象化,字形不再具有明确的表意成分,只是一般还承继了“母体字”的形或大部分形及音,意义上往往有了区别。比如甲骨文中的“每”,在编号“存二.七四四”的甲骨上,仍然是“母”的含义;但在“粹一一九五”甲骨上,则是“悔”的含义;在“甲六四一”和“甲三五九三”的甲骨上,是“晦”的含义。目前发现甲骨文中“每”的含义,限于此三种。但正因为“每”字不是地道的指事字,以致后来才有了常常、往往、虽、当、贪以及多数等等含义——不受因为是指事字的限制。

六,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把“每”解为“艸盛上出也。从屮,母声。”他解释“屮”是嫩草,“母”头上长嫩草,多少有些牵强附会了。可也怪不得他,老先生无缘见到甲骨文,且古时“每”与“茂”、“楙”等字同音,不少典籍多假借“每”字表达草木丰盛之状,如《左传》曰:“原田每每”;《魏都赋》云:“兰渚每每”,都是这个意思。所以,许慎就把“加笄于发”解为“屮”了。其实在更早的《诗经》里,“每”的含义已经是常、各、凡、虽了。后来一直到清代的学者,大多也觉得许慎对“每”的解释算是一家之言,但要往后排,《康熙字典》里就放在了对“每”解释的最后,而且字体上也与“每”有细微区别——上面是一点一横。
每字,通俗讲就是女人之每,每字就是女人过度到做人母的终结,从播簪,从母,造字夲意就是要每时每刻每秒都要注重自已在他人的母亲形象……